李劲对话许知远:个人、公益与时代变迁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年会(以下简称“2021年会”)于11月22日—24日在线上举办,主题为“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

李劲对话许知远:个人、公益与时代变迁
本文为基金会中心网理事李劲和北京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人许知远,在开幕主论坛上的特别对话,对话主题为“个人、公益与时代变迁”。
李劲:首先感谢知远接受我们的访谈。你这儿有一家基金会,我们很意外。大家知道你是独立的文化人,是多产的作家、深刻的思考者,办书店已经够忙、够难的了,为什么还要发起一家基金会?
许知远:当你遇到一个困难不好解决的时候,你就创造一个新的困难去转移注意力。当然,这是玩笑话。其实我们单向空间一直在做公益的事情,常年做各种免费沙龙,倡导公共阅读。
做基金会是有一个契机的。我们一直想伴随新一代的创作者们成长,所以我们有一个“水手计划”,去资助年轻的作家、摄影师、创作者,资助他们去世界不同的地方,产出拍摄、写作的作品,来促进中国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互相了解。做基金会跟这个计划一开始的念头直接相关。另外,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领导者——单向街基金会理事长许楠女士,她对此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正好就促成了单向街基金会诞生。
李劲:对慈善、对公益,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一般的理解是,做慈善公益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帮助弱势人群。但是我们注意到你们基金会不仅有水手计划,还有面向留守儿童的阅读计划,以及雅努斯翻译计划,这些项目都是在文化精神层面的。这和很多名人做公益的选择,如扶危济困、捐资助学等,很不一样。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是否跟你和团队对公益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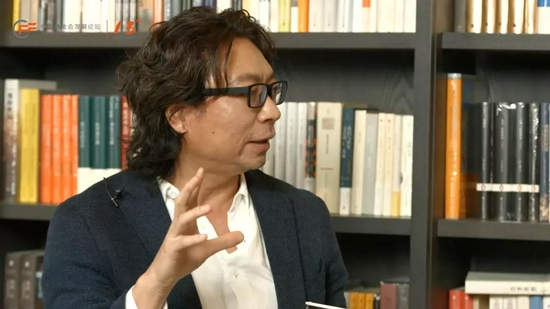
李劲对话许知远:个人、公益与时代变迁
许知远:我觉得每一家基金会都是创办人某种性格的延伸,也是既有组织性格的延伸。例如单向街基金会就是单向空间性格的延伸,我们致力于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成长性,想在我们更擅长的领域来发声。
基金会本来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我看过很多不同国家的基金会,有的资助艺术家、作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创造性人才。这跟扶危济困不冲突,是彼此弥补的关系。我们做尝试后,某种意义上也是希望能够在既有的环境中表达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更何况这些年轻的创作者的确需要某种支持,所以这就变成了我们的发展方向。
很多事物的观念是需要不断被打开的。当我们提到可持续发展时,第一个想到的是环境、现实怎么样,但我们精神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很重要。我认为,每个领域里都需要不断增加新的维度,使得既有的维度也能得到拓展。
单向街基金会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们资助年轻的翻译家和创作者,未来可能还有类似的新项目。这些领域经常被忽略,但又如此需要得到关注和支持。这几年,我们的新计划得到了不少回响,虽然范围不大,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试图用一种更独特的声音去做资助。

李劲对话许知远:个人、公益与时代变迁
李劲:你刚才谈到了几次“独特”。所以你认为,精神世界里多元的塑造或推进,其实也是公益的一部分?
许知远:当然。现代西方大学的诞生,各种研究机构的诞生,乃至博物馆的诞生,一开始都是由巨大的基金会推动的。基金会本来的任务就是多种多样的。
李劲:对基金会也好,对公益也好,多元确实是一个非常本质的特征。今天我来到单向空间,能感觉到一种公共的、特殊的气场,很多公益人有类似的理想主义。你常说“行动是(思想的)灵魂”,这些年你做单向空间以及基金会,实现了从一个思考者到行动者的转变。但同样作为行动者的公益人,有时会觉得有挫败感,因为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往往不被善待。你做单向空间这么多年,可能也会碰到同样的情况。你能跟我们公益同行分享一下,怎么对待或者处理这种焦虑?怎么自处?
许知远:慢慢就习惯了,好像也没有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来面对无力感。当然,有时候我们要区分一些东西。在潮流中做事情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各方的支持、关照,但很多东西并不是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而是潮流带来的。潮流发生转变时,正是考验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时刻。如果你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尽管没有那么多支持,你仍然会去尝试做一些事情,推动一些微小的改进。

李劲对话许知远:个人、公益与时代变迁
我们也不能天然赋予公益以及我们做的事情一种理想主义,不能认为做公益天然就有优越性或者更崇高性。这种感受应该是内在的需要,而不应该是外在的表现。所以这时候你需要寻找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办法来解决。
我们遇到困难时,在过去可以通过某种姿态或者表达与行动获得支持。但这种支持消失后,或者这种表达与姿态无法适应后,在经历很多挫败后,我们要想象新的社会语境,想象我们怎么在其中创造新的、吸引人的表达与行动,怎么寻找到新的支持者和同行者。
我们基金会支持的对象、资助方,都是我们的同行者,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共同体。我们要创造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和更多人产生新的、不断的同行,而不是只用固定的表达和姿态。这最后就变成了对自我更深入的检讨。有多少过去的成就,是来源于当时的时代潮流,而不完全是你自己的努力,你受惠于此;有多少是来自你自己独特的努力,然后能够坚持下来。
基金会是公益的理想主义的事情,但我们确实需要为理想赋予很多很现实的能力,甚至需要训练自己的现实能力来保护理想。这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很痛苦的挑战。
我自己有非常多的挫败感,但这也是促使我们成熟的契机。挫败和逆境,更能定义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李劲:谈到挫败感,你最近经历的一次挫败,能否给大家分享一下?
许知远:我创业一直挺有挫败感。我们很努力,表现的也还可以,但好像始终找不出一种更有效的商业能力,使得我们这样有公共精神的商业组织,能够更茁壮繁荣地成长。我们还是要去不断地面对财务等各方面的危机。而且,我当然希望能资助更多的创作者,但以我们现在的能力不足以做到。我们还希望基金会能促成更广泛的不同文化间的对话,这也在一点点地做,但肯定没有期望中那么快的到达。这些挫败都是日常中不断在发生的。
李劲:你已经算是很成功的知识分子,但在实际中还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会鼓励我们更多人去思考,重新审视自己。
许知远:审视自身,可能是面对困境最有效的办法。知道自己的困境,它会很痛苦,因为你要承认自己的无能和无奈。我觉得,一个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TA不做,会给TA带来更大的困扰。
李劲:我同意。过去一年,我自己也停下来,像你说的那样,在反思自己的局限性。反思可能很痛苦,但可以很有效地应对自己的挫败。
许知远:对。我们经常会高估自己,觉得成果是自己努力造成的,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是自己带来的。我们也会低估自己,觉得自己一事不可为。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挫败,但不应该被挫败腐蚀。被自己的挫败感腐蚀,其实是很舒服的感受,你会陷入一种自我悲壮或自我怜悯。在我们这一两代人身上,这样的东西经常会出现。所以,尽量尝试打破它们,虽然很难完全打破。
李劲:不应该让它成为我们不行动的理由,反而应该让它成为进一步行动的动力。
许知远:对。所以人很矛盾。我有时觉得行动是思想的灵魂,有时候又觉得不行动也挺好。如果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没能力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做什么也很重要,比乱做要好。但怎么区别做什么、不做什么、乱做什么,又说不清楚。有时我们在乱做中,好像又找到一线生机,找到新的可能性。我其实没那么多答案,都是在过程中“瞎来”。你要承受自己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瞎来”,始终具备某种真正的实验精神。
李劲:我们谈一谈你很喜欢的一个人物——梁启超。我们知道你在写《梁启超传》。梁启超这个人跟公益的关系很密切。他的儿子梁思成做文化保护,他的孙子梁从诫发起自然之友做环境保护。公益这个词传到中国,进入知识分子、普通人的视野,梁启超也起了很多作用。他写给光绪帝的《变法通议》中说中国应该像日本那样鼓励民众做公益,在《新民说》里也提到私益是公益的毛贼,应该跟私益做斗争。100多年前的中国,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这一代人做了很多启蒙工作,现在中国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公私之别、公共精神的创造,以及公共规则的创造,都跟从私到公的公益相关。这100多年来,我们中国人是否已经进步到可以进入现代公益的时代?
许知远:你的问题我也没有非常好的答案。但我觉得当年梁启超先生写《新民说》也好,做各种各样的行动也好,他们要创造的是一个社会。过去只有被统治的老百姓和统治的皇帝之间的区别,创造社会是要创造一个中间的阶层,需要各种各样的组织,需要各种各样新的道德和规则。这些是实践检验的结果,需要不断的行动。
怎样创造一个参与的组织,让大家关心超过自身私人利益之外的事情,并意识到公共利益跟自身利益的密切关系,这是需要不断实践的结果。我觉得我们从来都有做好准备,只是需要更充分的实践机会。
钱穆写过无锡村庄的故事,当年就有非常好的善堂,资助村子里穷人家的孩子去上学,是非常好的一个公益组织。赈灾时也有很多士绅捐款,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是那个时代民间的机制。
我们的社会随着现代技术和现代理念的发展,日渐成熟复杂,理念也更具体、更复杂。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与更充分的空间去实践这些理念。对于公共空间或社会空间,只要给予大家充分的时间,就会通向某种结果。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我对中国人的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有非常充分的信心。
李劲:有很多人认为,公益首先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只有对自己有好处了,才可能对他人有好处。先利己,才利他,而后利公。企业家群体也有这样的说法,说我们做公益,拿了很多资源出来,其实我们不能改变社会或改变世界,但至少我们自己改变了,这也挺不错。中国文化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以“我”为中心,到我熟悉的人,再到我不熟悉的人。如果把公和私分得很清楚,做公益就是由私到公的过程。基金会体现的是私人意志,用的是私人资金,但以公共服务为目的。我们怎么区分公私之别?怎么更好地适应由私到公的过程?
许知远:利他和寻求公共利益,从来就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利他,自己也同样会得到满足。一个人自我的需求能有多少?每个人都是在寻求利己和利他之间的某种平衡,我不觉得两者间有非常大的矛盾,何况利他一定是从你个人出发延伸的。
我们对文学艺术有更强的感受力,所以我们资助年轻的创作者。不是说做公益一定要把募来的钱给贫困山区,才是更有效的事情。我们团队不太了解也并不擅长做扶贫的事情,所以从自我的身份出发,我们资助创作者。但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资助对象的写作与描述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可能其中一个人写了一本关于大凉山的书,忽然就带来大家认知上的改变,带来了新的风潮。
某种意义上,我们的行为遵循了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不是说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冲着这件事的发生去做,而是有很多复杂的层次能够共同抵达。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会形成新的秩序,我们的感受也会超越自己眼前的事。例如无锡善堂,一开始就是钱家在做,后来扩展到更大,可能钱、王两家共同帮助了无锡,无锡又帮助到整个江苏,有一个自然秩序逐渐拓展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首先要给予自由空间去拓展,再慢慢抵达,而不是一上来就要创造一个完全“公”的项目,跟我个人毫无关系。那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历史中充满了这样的教训。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耐心等待。很多时候,我们的挫败正是耐心不足带来的。
李劲:单向空间书店一直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去年遇到疫情,经营上有困难,当时众筹自救,引起了社会关注。做“单向的朋友”的这些人,好多是中产阶层,是一批有思想、靠知识获得一定财富的人。这也是我们公益界很多人关注的群体,因为他们可能会成为中国第一批真正理性的捐赠人。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中央也认为要创造更多中产阶级,让社会形成纺锤形结构。中产阶级对未来中国公益的作用,你有什么观察?
许知远:现在中产阶级的概念受到非常大的挑战。一些社会学家有关社会演变过程的研究认为,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社会多样性的成长,进而带来更进步的理念,这个公式从长远来看仍然是成立的。过去三四十年,我们看到经济的成长,带来一个更多样的社会,也带来不同层次的价值观。
中产阶级受过更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更清楚公共利益和个人的关系。只有当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保证,公共生活更繁荣时,他们自身才会得到更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他们可以在这种公共的价值和多样的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那一块,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所以他们对这一切更敏感,会潜移默化地加入这样的行动。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有更多空间去想这件事。
我在别的国家看到一些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旧金山的芭蕾舞团需要支持,很多中产阶级捐赠,每个人捐的可能不多,就几百美金,但有非常多的人愿意捐赠,他们觉得这个芭蕾舞团是他们重要的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捐赠公共事务,因为公共事务的存在很重要。当时我们发起“单向的朋友”这个活动,大家可能也认为,这个空间在他们的生活中是重要的存在,所以选择成为我们的朋友。类似行为应该在社会中很多层面都在发生,而且应该有更多的发生。不应该只是姿态感,而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
李劲:你认为,对公共空间或公共生活的重视,可能是中产阶层更愿意参与公益的动机。我本来的判断或想象是,中产阶层可能更有价值观、价值感,会更加理性,更知道什么样的公益行为会带来成果。
许知远:他们会更知道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与他们个人生活的关系,因为他们能意识到什么样的生活最适合自己。他们的教育和生活会确认一些东西。大家会意识到,社会不均是社会不好的标志,是让人不安的事情,这不仅是出于同情,也是基于理性的判断。我们应该去创造一个更良善、更公正的社会,这些都是动力。
人的动机是蛮复杂的。好的制度和好的社会集体,应该去激发人身上这些良善、同情的动机,以及渴望看到丰沛生活的动机,并让这些动机得到生长。
李劲:在你说的社会机制中,公益行为或公益组织扮演了要紧的角色。
许知远:当然。一些更早发展基金会的国家,首先是从拥有巨大财富的商人开始的,去建立大学、医院、图书馆,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把它传承下去而不是分散下去,是一种罪恶。1889年安德鲁·卡耐基写了《财富的福音》,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而且那时候巨富的商人也受到很多舆论上的指控,散财也是平复舆论指控的一种方法,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动因。
慈善也好,基金会也好,都是社会组织的重要部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社会组织很繁荣的时候,基金会才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基金会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社会生态更繁盛,它才会更繁盛。
李劲:我们很多基金会的同行,还没有真正从社会生态来理解这个问题,还是自己埋头做事情。其实我们行业很早就呼吁资助,把资金分散出去,给更多的社会组织,这样整个的社会生态繁荣起来,才可能达到改造社会、实现良善的目标。
你从北大毕业的前后20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公益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种观点认为,公益活动、公益行为可以增加人的粘性,增加相互的关爱和信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去年你跟项飙对话时,谈到附近的消失、附近的重建,你本人也比较重视亲密关系的建立。但另一方面,社会变得越来越虚拟。最近“元宇宙”这个词非常火,我理解是把真实生活和虚拟生活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构建人和人之间在真实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公益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公益能够有所作为吗?
许知远:我们现在在向数字社会移民。当一个世界和时代发生很大的转变,大到民族国家,小到普通的商业组织,所有的组织都会因为这种巨大的变迁而重组。你看我们的工作环境,线上已经占到很大的部分。大家不来上班,我们组织也在运转。公益组织也只是大的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它也在发生对应的转变。但它的核心价值没有改变,仍然是希望促进公共利益的继续。但你要在新的环境中去理解,这个时代的新的公共利益是什么?我们稀缺什么?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我们能够表达和创造什么?只要核心价值没变,我们要去看待新的环境在发生什么变化。
比如现在我们的书店,完全不是过去书店的概念。我们要生产各种各样的内容,而且线上的业务远远超过线下,卖书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业务。这种变化在发生,但我们想传达的思想和精神,本质上没太大变化。公益组织也一样。人永远都需要社会资本,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你说大家在哀叹生活中的亲密淡了,但大家在微信上还可以跟陌生人建立亲密关系,热火朝天讨论一些问题。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到一个角度,找到自己对应的能力去实现亲密关系,这一切变得很难,但也是个很有意思的挑战。
阿道司·赫胥黎说过,曾经的异端邪说在一代人之后就变成了陈词滥调。你之前认为崭新的东西,在一代人之后就变得非常陈旧了,所以你要创造新的崭新。
李劲:公益的环境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面对不同的思潮,我们一些同行以前只看一个方向,看欧美怎么做。但现在我们自己的力量增长起来,可以更多来看我们过去是怎么做的,比如你提到的善堂。我最近也在研究中国慈善史,特别是明清和近代的,我发现中国有很多自己的实践和思想,只是我们没有认真关注。
许知远:60后、70后这代人,在中国刚开放的时候,不少人认为学习的对象只有西方。最终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精神资源是很丰富的。而且过去我们的想法很线性,认为事情会那样一步步发生,其实不是这样。很多人的挫败感正是因为,这个线性突然不是线性的了,变成迂回的了,甚至变成后退的了。这时候你就需要去找新的精神资源。
而且,我们不应该让一个行业变得孤立化。我们做的公益,是一个组织,需要组织的逻辑。现在新的商业公司的逻辑,已经不再模仿西方公司,有自己的一套。公益组织也一样面临着组织的演变。每个行业都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刷新自己的过程,需要艰苦的努力,而且需要广泛吸收各方面的资源。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我做这行,他做那行。每个行业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是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激励人、启发人,然后大家一起达到目标。
所有的行业也都需要杰出人物,一些行业经常被一些天才人物改变。特别是有独特性的人物,会重新洗刷大家对行业的理解。比如项飙,他突然激发了这一代年轻人对人类学的兴趣。他也不是刻意的,只是因为上了节目,有一个很好的释放,大家意识到有这么个事情。你们这个行业也一样,我觉得需要一些非常有感召力的人物的加入,带来一些新的表达,吸引大家加入其中。
李劲:公益的破圈一直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词叫公益圈,好像我们是个圈子,公益只是我们公益人做的事情。
许知远:封闭系统是一个最有害的问题。所有的封闭系统都会带来某种停滞萎缩。我们不能内卷,我们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系统。
李劲:刚才你提到了要寻求更多精神资源,向我们自己的历史、向企业学习,我相信这些对我们同行会很有启发。像你说的,我们这一两代人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期,当时只有一个学习对象,现在发现不够,这很容易导致内卷。
许知远:中国的过往有很多可以激发我们的东西,包括你刚才提到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以及你说我们对自己社会的理解,我们自己的一些杰出的头脑,都会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
李劲:过去二三十年,当我们在对外开放、向外面学习的时候,其实忘掉了这些。
许知远: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人都是这样的,然后你会重新地自我寻找,重新理解自己的过去。这是随年龄而到来的认知。
李劲:提到年龄或者代际差异,我最近接触很多做公益的年轻人,也跟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交流,发现他们的思想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边际,反而非常清晰。对做公益的年轻人或者年轻人做公益,你有没有什么想讲的话?
许知远:没有。我特别讨厌自己有一天会产生说教欲,我完全没有说教的欲望,而且我对代际感觉不是很强烈,我觉得大家都是个体。
如果我能跟梁启超产生交流,那么年轻一代完全可以跟任何时代的人交流。每代人中都有非常杰出的人物,不管是商业还是公益方面。我认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提供多样的选择,让个体各自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而不是认为,只有一种选择是对的。
如今年轻一代,是在一个相对信息富足和物质富足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某些人会非常杰出,因为起步时的困境没那么多,一开始就有更大的视野。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社会、对新一代人抱有信心。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批判。我们应该批判过去、批判现在、批判未来,怀有批判性,保持批判思维。但同时在背后是怀有信念,怀有对我们的社会本身的信念。
来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公众号
编辑:王俊杰 审编:admin